本帖最后由 大爱无言 于 2014-4-5 11:18 编辑
为着“根”的循迹
——谨以此文祭奠先祖们
松江水暖,杏红柳翠。一踏上春光明媚的古镇街道,就感受到由衷的温暖。不是此地人,却有种发自心底的亲近感。姑苏吴江松陵,一个魂牵梦萦的江南水乡。时过三年,又来到这个地方。 松陵,镇上一座密植松树的小丘岗。这是一座镇名因其陵而得的丘岗。丘岗正面路边,费孝通在一块大沙石上写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的字句,追悼着湮没在风烟中的亲人。我不知道这儿曾经安放了那些人,但清楚我的祖先一定是在这儿与他们一道长眠的。丘陵上没有墓碑,它们早被当“四旧”给毁掉,松树是在那场该死要命的浩劫后重新种植的。原来的坟茔墓碑不在了,但丘岗上松树却长得很健壮。因为它们生长于深厚的文化泥土中,它们的根下有着更深的根。 祖先是从临近吴江的浙江乌程迁徙过来的,时间是在元末明初。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在这片明丽富庶的水乡泽国上劳作、生活、繁衍。明、清两朝“期间科甲蝉联,文人辈出,他们中走出了一百四十九位文学家,作品集百余部,并且产生了科举上的‘沈氏五凤‘和文学创作上的‘沈氏八龙’”,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学家族。其中有被誉为“汤词沈律”的曲坛巨匠,也有被称为一袖清风的政坛“驴车宰相”,还有中国产生于江南的第一个“疏香”女子诗社及其主人宛君。毋庸讳言,他们中亦有“习娇淫,尚刻礉”的倾败家业者。明清鼎革,遭受变乱,家族乃始分别迁徙、流离他乡,散枝发叶。又经数次战乱及民国、共和国之替代,族裔子孙遍布大江南北十数省,而在故乡却没有能够留下过多的痕迹。以致多数后人皆知祖籍吴江而少临吴江。 因为这样,我来了。不是为着倾慕那些曾经声鹊一时而终归流逝的大家名人,也不是为观家族变化而折射江山兴替之光,更不是为着人生修为的经验教训,而是为着循觅自己的根。 血缘自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它几乎不用什么号召,在幂幂心灵里似乎总会有一种呼唤,把你引向那里。无论你身在何处,天有多高,地有多远,也不管你曾在那里生活与否,那份深刻埋藏在心里,流淌在血液中的根基乡情总是割不断的。于是,身在远方的“游子”,时不时地会来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根”是个人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根是民族文化的,她同我们的传统文化并蒂相连,一脉传承。没有了这个民族的、大众的,个人的“根”也就显得渺小而无所谓轻重了。祖先们喜爱古典文学,也许他们的初衷目的并非很崇高,许多人也仅就是出于个人的嗜好。一个传承几百年的文学家族尝若没有这很多个个人的喜好,甚者还有仕途中年就辞官归里,专修词律的人,是不可能延绵相袭的。但也就是这种家族性的个人文学喜好,才构成了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家族式群体传承。也正是由于这种群体性的传承,才为我们的古典文学增砖添瓦,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学在唐诗、宋词、元曲后,开始向传奇、戏剧的过渡和规范发展。以致在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也最终造就了被誉为“国粹”的京剧。 白天,松陵公园里上演着吴调越曲。尽管我这个“外乡人”独自一人在那里,听不清台上的戏文词句,但它纾缓流畅的情调旋律却深深地攫住了我的心。坐在树荫下,闭上眼,静静地聆听、感觉、欣赏,还不住地跟随音律节拍左右地晃动着身躯。因为,因为那是诗礼相传的家风,是汨汨血脉的流淌,是文化这枝“根”发出的声音。 吴江的夜也是温婉深情的。吴江公园棕榈树下一对老年夫妇坐在平整光滑的石板椅上,一只团团雪白的小狗静静地蜷伏在脚下。在微弱的灯光照耀下,老人轻声哼着越曲,间或说着些呢喃的吴侬软语。在这个月亮刚圆的时候,她的神情很安闲甜蜜,更像是那种春杏女儿在谈恋爱。活色生香的夜晚广场舞乐曲也多是富于律动变化的江南丝竹调,而少了些风动全国的“江南style”。看来牧马人雄浑激动的奔驰节奏并没有能改变他们清雅婉柔的风尚。这,就是江南文化的熏陶和风采。 听房东大娘说祖上那块宅地荒芜了很多很多年,那位痴呆的看守人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地块也被政府收去盖高楼了。一个曾经的声誉望族,最后的痕迹也在星月时光的发展变化中黯然消失了。这,是真的吗? 费孝通的题字说得好:“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生长于斯而传承于斯。民族的,乡土的,也必然是“根”上的。由是,这个文化沿袭的“根”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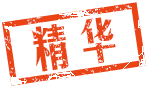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