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桃 花
苏翠玉
桃花的美,都是庄子里的人默认的:明眸皓齿,鹅蛋脸,肌肤如脂,身材丰腴,青葱细指,模样周正得很。提到老张家,很多人总是在暗地里摇头,说姑娘生在他家,白瞎了这孩子。
桃花性子好,家里家外算是一把好手。只是家里不景气,父亲长年卧病,母亲操劳家里的里里外外,家里的两间茅草屋风雨飘摇。
家里还有一位哥哥,还算是白净,青春的那阵子,殊不知庄子里多少女子芳心暗许,若不是家贫,嫂子早就有了。父亲为这事也是一病不起,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哥哥起先还不曾在意,在身边的同龄人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哥哥也有些急了,整日垂头不再言语。
说亲的也找一茬又一茬,婚事却也是黄了一次又一次。连村头的懒姑娘胖白荷也羞答答回了媒人,说人是好的,但家太穷。虽说胖白荷是那种连庄上的癞二狗都不想搭理的主,居然也回了哥哥,这次真急坏了老张家。
桃花她娘发了毒誓,不问什么代价,得给儿子说门亲。
日子细长,碎碎念,似流水般的波澜不惊。 庄子里的那些愣头青也是喜欢桃花,也有几个常去献殷勤的,挑水、劈材,凡是力气活都会有人抢着干。但是桃花不怎么爱搭理他们。桃花心里有个模子,找个能像村头的教书先生那样的。记得那年,城里刚分下来教书先生刚来这个村子,干净的白衣服散着说不上来的香,阳光下,先生眯着小眼,细嫩白净,一笑露出两个小虎牙,一脸的阳光,斯斯文文的,桃花隔着一树的梨花,心里暗许。能找个类似的就好了。
这几天娘背着桃花,总和她爸小声嘀咕什么,神色时而暗喜,时而悲伤。但每次见桃花来时总闭口不言。娘这两天核桃似的脸上偶尔也会舒展些,只是他爹一直紧锁眉头,唉声叹气的,反复嘀咕着这么一句:"这下子可苦了孩子。"桃花不懂,也没多问。一味埋头做事,心里有些疑疑惑惑的。
爹几次欲言又止,见了桃花却张不开嘴。还是娘狠心,哭哭啼啼的将合计了多日的事断断续续地告诉了她,村里的媒婆李寡妇颠着小脚喜形于色地跟她娘说了一门亲,只说了“双交亲”。桃花一听一下子跌坐在床上,这就是农村人嘴里最恶毒的“换亲”了。刺骨的凉一下子由指尖逼进心脏,桃花怎么也不信,娘能这么狠的答应下来。真是即将嫁出去的姑娘也就成了泼出去的水,那还管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桃花心都碎了,娘说的时候也红了眼眶,娘儿俩泪眼涟涟的看着,只是桃花就是不松口,娘用哀求的目光看着,就这样僵持了一个晚上,娘儿俩和着衣服睡着的。几天后的晚饭,娘破天荒的做了一桌子的菜,爹也精神抖擞坐在桌子旁,桃花心里有数,只是不言语。哥哥更是难得剃了头刮了胡子,人也是成熟中透着点沧桑,还是耐看的。一家人难得正式吃顿饭。爹喝了点酒,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列祖列宗,一辈子混得不如人,没本事挣钱,害得儿子都讨不到媳妇。爹一贯疼桃花,小时候老背着哥哥留些好吃的给桃花。爹的一哭诉,把桃花心都哭慌啦。娘看准了火候,叫哥跪在桃花面前,哥就这么望着桃花,低着头不言语。桃花心一酸,心里冷透了,知道这一辈子就这么了。心里还是希望"双交亲"那头也是穷的。
日子很快就定下了,在下月初八,是娘特意碎着小步子请村头的香头合的日子。说是能成还能旺两家。
哥哥在等的那几日偶尔也会露个笑脸,农村的女子命贱,桃花总是恨恨地想着,心里却有说不上来的苍凉。
日子一转眼就到了,看人的地选在李寡妇家,娘说家里的两间破草房子待不了客,那家的姑娘要是看对了眼,兴许不会那般的不情愿,省得双方还得多费周折。
一大早,娘就吩咐哥洗澡洗头,给哥整了一身新的,还别说哥被这么一收拾,还真有点帅气。娘也给桃花置了一身,新褂子也是最新流行的款,粉粉的,掐腰小灯笼袖,正是桃花想了很久没舍得买的那种。胖白荷前几日也穿了一件,只是硬生生把上身勒出了三段来。连村里的狗瞧了都对她多吠了几声,胖白荷也扭着大肥腿在桃花那里显摆了一回,那时桃花还惋惜那件新衣裳来着,这会怎么看都觉得刺眼。
桃花看着小褂子发了一会呆,摸着料子,要是搁在平时,准能美死。桃花叹了口气,在房里随手拿了一件昔日旧衣裳,心里很是矛盾,既希望哥哥能相中,又怕自己被相中。
在李寡妇的一再张罗下,亲相的还算成功。那头早就等着了,桃花一露脸,那头便一阵骚动,尽管桃花身着半旧的衣裳,但美是怎么也盖不住的。等人坐定了,桃花冷冷的扫了一眼,新嫂子长相平平,是那种淹在人海里便找不到的那种,矮矮的,略有点憨厚敦实。估计娘相当满意,是标准的那种脸大,屁股大,关键是好生养的那类。
如若家境好点,估计哥哥怎么也不会挑上她的。桃花心里有些不自在,坐在那里不出声,也只好上下打量着。
嫂子低眉顺眼的,哥哥也瞧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总之没有什么欢喜的神色。倒是新嫂子在打量过哥哥后,脸上倒晕出一些红来,大抵是满意的,要不怎么看她,都觉得她怎么掩饰不了眼里的欣喜。桃花的心里一紧,赶紧打量换给自己的那个人:身材中等,略显单薄,脸和嫂子略微相似,算不得好看,也挑不出较大的毛病,就是年纪有些大,听媒婆说略大个七八岁的。桃花虽说很不情愿,但媒人一再说那方还有三间大瓦房,只是家里还有个兄弟。看娘的一脸喜色,桃花咬牙,应下了这门亲。双方定下了日子,就在年下,说是到时候能杀头猪,简单的摆上几桌算是也热闹了一番。
定的日子说到就到了,哥哥一脸喜色,母亲也好歹把家收拾得一新,就坐等新嫂子过门了。爹一脸落寞,私下里把攒了几年的百十来块钱悄悄地塞给了桃花,这次桃花没有像小时候那样接着,而是悄无声息的落了泪。爹手一哆嗦,钱散了一地,桃花逃了出来,不忍心看爹的伤心,更不想领这份情。爹老泪纵横的杵在屋里,一动不动。
接亲的车子来了,桃花一狠心,咬紧牙愣是没流一滴泪,娘心里明白,姑娘心里有恨。为了儿子,娘也作了这一回孽。装着喜滋滋的待人接客去了。
桃花进了新嫂子家,果然如媒人所说,三间青砖小瓦房,家里也收拾得整齐,比家里还强些。桃花心里有些疑惑,若此这般,竟也用得着换亲?
一切顺势而行,拜堂成亲,也照了寻常人家的办,就人丑了点,也不见得亏了桃花多少。
桃花坐在新娘房里暗自猜想:这会子嫂子会不会懊悔呢,毕竟家里相较来说,穷真的是穷狠了。就这么热热闹闹的折腾了一天,夜幕就这么死寂般的降临了。外面的老老少少吃的油光满面,打着饱嗝三三五五的散尽了。
村子的夜说黑就黑了下来,平常八九点钟便没了声息。随着酒气的袭来,最后一阵人送来了新郎,桃花就听见关门的声,抬头时桃花掀开了红头盖,一张沧桑而又衰老的男人脸映入眼帘,桃花一惊,脱口便问:“你是谁?怎么进了这个房间?”随着视线的下移,桃花惊惧的发现穿着新郎服的不是相亲看的那个大几岁的男人,比当天瞧得要老得多。桃花惊悚的瞧出了这个新郎还瘸了条腿。
就在桃花陷入沉思之际,瘸子踱了进来,面对桃花的质疑,瘸子一五一十地说:“我是你男人,换亲的男人,实话跟你说吧,相亲的人是我弟弟。如今拜了堂,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妹子你就认了吧。”
桃花一急心口猛地疼了起来,泪却无声息地流了出来。瘸子却也不介意,憨憨一笑,说:“姑娘,你又不是白嫁到我家的,俺妹子不也给了你哥?时候不早了,该睡了。”说着就伸手来拽挑花,桃花猛得站了起来。死死地攥着本来用来挑盖头的秤杆,眸子里透露出绝望的寒光让瘸子脊背发了凉,瘸子一眼就看出了桃花的狠劲,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也不用怕,今天我不碰你。不过你得记得踏进这个门你就是我的人,这个事实就是你死了,也改不了的。”
许是累很了,瘸子一着床便睡熟了,还打着响响的呼噜,桃花悬着的心终是卸了下来,可手里的秤无论如何不敢放下,就这样拿着秤倚着墙半醒半睡的熬着。一晃也就天亮了,外面早就忙开了,洗刷声中透着喜气,桃花痴痴地坐着,瘸子不声不响地爬了起来,在一旁忙着什么。桃花不经意间看见瘸子抽出新被褥里的白帕子,将胳膊刺破,血在白帕子上开了一朵朵妖艳的花,桃花猛的醒悟过来,伸手去抢瘸子的喜帕,瘸子眼里闪过一丝诡谲的笑,用尽力气推开了桃花,一闪便出了门。桃花跌坐在床上,一股凉从指尖逼进心脏,这辈子完了!桃花麻木地枯坐着,门外早已响着喜庆的鞭炮声,婆婆尖细而爽快的招呼着早就在门外张望的村里的老老少少,拿出瘸子递来的喜帕,笑盈盈地递给门口的左邻右舍的妇女,一个个喜滋滋地翻看评论着这新奇而又平常的物件,嘴里咿咿呀呀的品着,论着,都说瘸子小有福气。新娘这么美难得还是个全乎的,在啧啧赞叹中似乎还有些可惜。
桃花一整天都没出门,倚在婚房的床架上,不吃也不喝。婆婆颠着小脚细声慢语的劝着,说得都是些软乎话,瘸子却不在意,他心里明白,桃花再怎么倔,过了昨夜传了喜帕,不怕她不从。这女人心气大,更何况瘸子知道桃花美得有些出格,在这个庄子里,除了发了横财的二喜离了自家老娘们,从城里带来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妖精外,村里小媳妇没人能把桃花比下去。
照例第二天是回门的日子,新嫂子在哥哥的陪同下早早的回了门,桃花却熬红了眼,在房里不肯出来,桃花在房里哭闹着要见当日相亲的人,嫂子一脸尴尬,哥哥则红了眼框。
婆婆指使瘸子的兄弟去劝劝,刚踏进新房,桃花看见那日相亲的兄弟便跳了起来,大声地责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桃花熬红了双眼,目光犀利中带着狠毒,往日柔美的脸庞全是泪水,瘸子的兄弟痴痴地看着桃花,低着头不敢言语,只是支支吾吾说不上话来,索性拔腿就走。桃花以死相逼,今日如若回门,只跟瘸子的兄弟去,不然就不回这个门了,家里的五亲六眷一下子愣住了,农村人办喜事十分讲究,不回门怎么行,桃花这次豁出命来,婆婆显然慌了神,一大家子议了半天不知怎么办好,瘸子铁青了脸恨恨地说:“二弟,这门你回,哥请你再帮回忙,不过你得记住,这是你嫂子。生是哥的人,死是哥的鬼。”
那天风缓了下来,大地在薄薄的夜霜下显得更加冷彻,柱子带着桃花回了一趟门。柱子腼腆,也瞧出桃花娘眼里的躲躲散散的疑惑。日头一下子就西下了,桃花娘早早的就催桃花他们回去,直到哥嫂回来,桃花还没有回家的意思,娘急得直催促。新婚回门没有带月归的理,娘说这不吉利,桃花淡淡地说:“娘,今儿就不回去了,今天和新姑爷就住娘家了。今儿你撵闺女走,明儿就等着替闺女烧烧纸吧。”
娘怔住了,鼻子一酸,泪就下来了,背过脸就抹了泪。颠着小脚收拾床铺去了,晚上老两口去了李二奶家将就睡了一夜。这一夜诡异得很,桃花望着柱子,说睡吧。二柱涨红了脸,就是不敢过去,熬了一夜。倒是桃花倒头就睡,一夜不曾醒过。
一大早,娘就催二人回去。回到婆家,家里早就炸开了锅,村里的妇女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婆婆灰头冷脸的,瘸子的脸更是狰狞得可怕。桃花一脸的轻快,进门就喊:“娘,我们回来了。”婆婆剜一眼桃花,对柱子说:“今天就跟西头二奶奶家的大壮去上海打工去吧。”柱子愣了一下,转脸想解释来着,一眼瞧见哥眼里蹦出的毒,一下子慌了神:“嗯。”一声走开了,桃花的欢喜一下子挂不住了,眼睛的光一点点淡了下去。
桃花依旧住进了瘸子的屋里,每夜总是熬着,守着,瘸了的人总有些狠劲,不知听了谁嚼得舌根子,对桃花总是拳脚相加,每每发了狂,总要闹个人仰马翻的。婆婆偶尔看不下了,还心疼的劝劝。打得多了,婆婆也懒得管了,总不忘叮嘱几句:“别打残了,女人就这么个命噢。”桃花的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瘸子总想听桃花服个软,可桃花从不吱一声。
瘸子打狠了,桃花反而咯咯的笑,笑的瘆瘆的。瘸子最听不得,每每寻个借口逃开了。
日子就这样絮絮叨叨地过了下去。
转眼又是一年,村里打工的人陆陆续续的回来了,桃花挺着肚子漂洗衣服,洗完桃花吃力地搬着木桶,走向家里。“嫂子,我来。”柱子赶忙接过盆,桃花慌忙松手,有些手足无措。桃花打量柱子,或许城里的水养人,柱子白了,也壮实了些。桃花羞涩中有些信息。终于回来了,心里的盼一下子落地了。
桃花喜滋滋地踱着,刚进门,就发现平时冷清的家里挤满了人。一个略瘦的姑娘红着脸坐在家里,村里平时不怎么往来的亲戚老道的扯着家长里短。桃花一下子有了不详的预感,果然,女孩是柱子打工带回的女人,说是不嫌弃柱子家穷的,桃花一下子坐在地上,心一点点的凉,望着村口悠远的前方,没有了一丝希望。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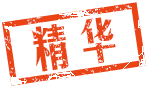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