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爱无言 于 2014-8-30 14:43 编辑
硕 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句《诗经》里面的诗句,人们是再熟悉不过了。古代的先民们对长得胖头胖脑,肥硕溜圆的大老鼠非常痛恨。它们一身灰毛,尖嘴豆眼,贪婪、无耻,老在深夜隐秘地活动,损害庄稼物什,传播疾病。也许从那个时候起,老鼠就成为一种从形到神、直到骨子里都肮脏不已的丑恶物种了。以至在《诗经》里大凡说到老鼠的事,总是义愤填膺,鞭挞不已。 但事物也不是那么单一纯粹的。南宋的刘敬叔在他的《异苑》里却写了这么一件事:说在景帝年间,东阳发大水。一位叫蔡喜夫的人为躲避洪灾跑到陇南。夜间,有一只型如狗崽的大老鼠,浮水而来,蜷伏到其家奴床角。家奴见状顿生怜悯之心,“愍而不怒”,并且每天都拿些剩余的食物喂它,直到大水退去。蔡喜夫返回家园,那只老鼠也随同他一道归去。它用两只前爪捧着一只青布小囊,里面装着一枚三寸许珠,放在家奴的床前,并且嘴里轻声啾啾不已,象要对家奴说些什么。从此后,那只老鼠就与他家常来常往,还能向他们表知祸福。 无独有偶,在关中地区有个传闻,说当年孔夫子到各国云游,来到潼关。一天早晨,看见田边有一群老鼠拱着前爪站立,对日作揖。这位老夫子顿时有所感悟,说秦地的老鼠尚且懂得礼仪,想来人也不会不知,便打消了去秦地游说的念头,返道而回鲁国去了。关于这件事,在道家老祖之一关伊子的著述《三极》篇和刘敬叔的《异苑》中也都有相似的记载。 在这两个事情中的老鼠似乎很有教养,懂得礼仪和情感,非但不令人厌恶,反而让人颇生爱怜。看来被人憎恨的老鼠,也还具有一点良好的品性。当然,孔夫子的那个事只是个传说,道家的言谈显得玄妙,刘敬叔的《异苑》也是专门写些神怪灵异的事情,让人不得相信。读此书,闻此事,也就仅当茶余饭后罢了,谁也不会认真。至于世上有没有对日作揖的老鼠谁也不在意。 可这世上偏偏还就真有“对日作揖”的“老鼠”。在非洲沙漠地区,有种动物叫猫鼬。其身板形态和习性很象大老鼠。它们也是群居,每天早晨起来,便一溜儿挺直瘦肚皮站在土埂上,前爪放在胸前,朝着刚升起的太阳一动不动。这是因为它们体内没有脂肪,不能大量积蓄热能,经过一夜的折腾,热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必须尽快晒太阳补充。因而它们“对日”就不会是礼敬“作揖”,而是敞开肚皮,增大受热面积。这种动物在那时的关东地区到底有没有,不好说,但关东地区也是常刮风沙的。 虽然这些个“老鼠”不那么惹人厌恶憎恨,但它们毕竟还是老鼠,怎么也改变不了人们对老鼠这个“类”的丑恶印象和诅咒。而要命的是,这个诅咒绝不只是对着老鼠本身,它扩展到了社会人文。 把老鼠与人联系起来痛骂,并见诸于文字,是从《诗经》开始的。除了《硕鼠》外,《相鼠》篇骂得还要痛快: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有些大官们饱读诗书,满口尊卑礼仪,暗地里却搞些见不得天的龌龊事。这怎么不受到老百姓的唾骂呢?这样的大官们就跟大老鼠一样,对物质金钱贪得无厌,干着些损害社会的事。尽管老鼠有所谓“对日作揖”的礼仪,和捧囊报恩的情感美化记载和传说,但那些都远远不足以抵消它们的丑恶卑鄙。 “对日作揖”的大老鼠,从先秦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直到如今甚而更厉害了。一只“大老鼠”动辄成十上百个亿,还有众多的小老鼠。这些老鼠们还都曾“对日作揖”,先前还表现得很美好,或许还非常有人情味。可一旦它们到了无拘无束的深夜,就啥龌龊的事都干得出来了。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逝将去女,适彼乐国。逝将去女,适彼乐郊。”《诗经》里回沓往复,发出了这样情感炽热的呼喊。面对这样的硕鼠,老百姓毫无办法,如果一任这些硕鼠贪婪下去,他们只怕最终连性命都不保。所以他们要离开魏国,去寻找一个适宜他们生存的“乐土”。而在如今,老百姓能逃到哪儿去呢?“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就必然要离心离德,亡党亡国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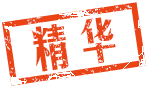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