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葚熟了的时候
文●苏宝大
小满一到,桑葚渐熟。
每到桑葚熟了的时候,我站在桑葚树的底下,仰望那缀满枝头的颗颗桑葚,由青转红,由红转紫,我的脑海立马浮生出一个人来。而他却过早地殇折了,就像夜间苍穹之中划过的一颗流星,只一丝短暂而微弱的痕迹。
在那清汤寡水的六十年代,对于乡下的孩子们来说,天生的泼皮。但饥饿常常困扰着他们。吃,一直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头等大事。家中一日三顿,能填饱肚子就是幸福。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的荤菜。所以那时候乡下的孩子从早到晚忙活的就为了一张馋嘴。
在农村,村内,村外,处处有小河,有小沟。故乡的水和土,就这么的神秘。随便开挖一口池塘,几场春雨,漫过池塘,历经数月,就会有鱼有虾有螺蛳,甚至还有河蚌。
立了夏,天转暖,就是乡下娃儿们解馋的时候到了。
脱去衣服,拿个踢罾,扛上趟网,踫在水里,中午或晚上,从各家各户厨房里准能飘散出乡村的野味来。大人们从田间归来,桌上准有几碗不是罗伙儿,就是鳑鲏儿,不是长鱼,就是鳅鱼的下酒下饭的荤菜。
乡下人,只知道一溜溜地生,从没得到娇生惯养。
父母们白天黑夜忙着大集体干农活,无暇顾及到留在家中的孩子。好在乡下的小孩,自有天生的野性。广袤的田野下,见河,踫河,见树,爬树,犹如鸟儿,蓝天中飞翔。他们下河,爬树,常遇不测,却能凭借他们那天生聪慧的头脑来判断或处置,用句乡下的土话:“能杀猪,就能翻肠。”但也有不幸运的,最终他们还是没能逃脱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过早的殇折了。
庄上的六伙,那年八虚岁。上有五个哥哥,六伙最小。六伙皮包骨头的瘦,一身黑不溜秋。他人虽小,头大,胆也大。走在巷子上,如一阵风。
一日,相命先生在村口撞见六伙的面。发现六伙身后,鸡犬狗不宁,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与常人不一般。相命先生回头朝六伙的背影竖了竖大拇指,说,此人长大了不得了。相命的先生临出庄时,与一老人丢下一句话:“此人要么出贵,要么包芦菲。”(芦菲:家乡方言,芦席)相命的先生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六伙,要么出人头地做贵人,要么见阎王。
桑葚熟了的时候,庄上的六伙,他从没捡拾过一粒地上被人踩过或被蚂蚁爬过的桑葚吃。他人虽瘦,他爬树时,“噌”,一眨眼,就上去了,像猴子。庄上跟他玩得好的伙伴,只能眼巴巴地仰望那满树满枝又大又黑的桑葚儿,等他稳坐在桑树的枝丫间吃饱了,他才慢悠悠摘几颗生涩的桑葚,按人头,按数量,抛洒下来。那时候,他就是村中的“孩子王”,鸡狗见了他还让三分呢。
记得村上一徐姓人家,养了只很凶猛的黑色疯母狗。我们那时只要是走到了那条巷子上,只要那条母狗发觉了我们,准会疯狂的追赶着我们,准会糟糕地吓得我们丢魂落魄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溜。到了深夜里,准会做起与这条疯狗有关的噩梦来。
可蹊跷得很,这徐姓家的疯母狗,不知怎的,只要它一撞见六伙,疯狗的情形立马相反了。疯狗在六伙前面逃,六伙在疯狗后面追。疯狗一会儿逃没了。疯狗准会躲藏于草垛,三天三夜不敢出来屙屎撒尿。
庄上的单身汉“豁嘴子”大叔,就承认了六伙的本事。“豁嘴子”大叔不可否认地老当着我们和六伙的面,夸奖起他有多大多大的本事,甚至无可置疑六伙对他家餐桌上的贡献。
村上庙的东北侧,有口见方的深池塘。深池塘约三四亩。这口池塘,是早年村上周围人家砌房子,为了取土的方便,就一个跟着一个地开挖。由于这口池塘处村的中央,夏天一到,小伙伴们总喜欢聚到这口池塘里,洗澡,摸螺蛳,摸小鱼小虾。
据我所知,这口池塘里,曾经吞噬过几个鲜活的幼小的生命。
这口池塘的四周,长满歪歪扭扭斑痕累累的老杨柳。老杨柳枝条袅袅娜娜一直柔软地垂挂于水面,有一些枝条一直伸至池塘的水里。这口池塘夜晚人至,觉得阴森森的恐怖。
但庄上的六伙,胆大也聪明。他知道伸进到水里的柳枝条上,吸浮着肥大的螺蛳。
当每年立夏过后,河水还凉飕飕的,六伙就敢一人踫到那总让我们感到恐怖的深池塘里,从一根根的柳条上,摘取一颗颗肥大的螺蛳。
他家每年总抢在别人家前,先吃上几顿螺蛳肉开了荤。这时候,无论是中午或晚上,人们只要是走近六伙家的那条巷子上,老远鼻子里准会窜来一股香香的螺蛳或小鱼儿的鲜味,使得有人曾经长久徘徊于六伙家的门前,闻着那香喷喷的美味,久久不愿离去。我每闻着他家的鲜味,就特别羡慕六伙的胆量和本领。
一日,太阳西坠,满天的星星儿挂上了天空。大人们都忙碌着从田间赶回了家,烧好了晚饭,捧上了饭碗,悠闲地站在巷子上吃着晚饭。
可那一晚,跟往常不一样。庄上一些大树的枝头上,喜鹊儿们烦躁忙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有小孩还在外疯玩未归家的大人们,听着喜鹊在枝头叽叽喳喳叫着,突然心里头变得七上八下。他们匆忙丢下碗筷,都在着急寻找自家未归的孩子。好像村里今晚有什么不祥之事将要发生。
果然不假,从漆黑的巷子里,传出一个不好的消息——六伙失踪了。
全村人出动,提着马灯的,点着火把的,大家都在寻找六伙。
找了一晚上,六伙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
第二天蒙蒙亮,“豁嘴子”大叔发现了六伙仰面漂浮在了村中央那口深池塘的水面上。池塘周围,立马挤满了人……
当天下午,六伙的父亲找了邻家一张破旧的芦菲。
我静静地默默地走到六伙身旁,跪下,见六伙双眼睁着,他紫灰色的脸,紫灰色的小手,手心里紧紧攥着几片细细的柳叶。他的父亲母亲和本家几位婶娘们,趴在六伙的身旁,正嚎啕大哭。
太阳要下山了。
“豁嘴子”大叔将伏在六伙身上痛哭的父亲母亲和婶娘们扒开,“豁嘴子”大叔将六伙慢慢卷进到破旧的芦菲里,并用绳带紧紧捆扎了起来。
“豁嘴子”大叔,带上一把大锹,背着芦菲中瘦弱得皮包骨头的六伙,向着太阳下山的反方向走去,将六伙送到了村东头那片三面环水,荒凉凄凄的“乱坟葬”之地。
“八升命,求不得一斗。”那一年,六伙八虚岁,正是桑葚熟了的时候。
六伙没有上过一天的学,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子。他就叫——六伙。
六伙死后,有人想起相命先生那一语成谶的话来:“要么出贵,要么包芦菲。”唉!可怜的六伙哎,你怎么就选择了包芦菲哩。
几年后,我去乡里读书了。每每路过那个三面环水的“乱坟葬”之地,我总会自然而然停下来,隔着河,朝那矮矮的坟堆,远远望去……
后来,我多年不去看那矮坟了。突然有一天路过,却发现六伙土坟一侧,出奇地生出一棵桑葚树来,那年有手膀般粗壮了。后来,这棵桑葚树,一年比一年地高大,一年比一年地旺盛,并在每一年的小满后,树的枝枝丫丫挂满了甜润的颗颗桑葚来。看着熟了的桑葚,我又想起了曾经的六伙,然后我会驻足,静静凝视荒草之中的那座矮坟良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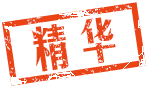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