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的本意指和谐的声音,用韵就是读起来听起来要和谐。和谐,并不是韵母相同就和谐,韵母不同就不和谐那样简单,韵母相同的字,在与声母配合后,读音方式会发生改变,有的不一定就能和谐,比如:风、蓬、蒙与生、明、争,虽然它们的韵母相同,但如果混用在一起押韵,就感觉很不和谐。有些字,它们的韵母不同,但由于读音方式相近,则往往又是和谐的,比如:“衣与鱼”,它们的韵母不同,如果用现代的语音来读就非常和谐,所以有的韵表把它们归为一个韵部,这是有道理的。比如诗经:《简兮》“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中,“翟与龠、爵”,《蓼萧》“蓼彼萧斯,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中,“湑与写(带助词押长尾韵)”,《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中“夜与日。居”,它们韵脚上的字,虽然韵母不同,古今也从未把之归入同一个韵部,但在我们今天读起来仍和谐可押。
故和谐与否,不但与韵母有关,还与声母的配合及发音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再比如在《现代汉语》中,这几个读音完全相同的字“合、阖、禾、河”,由于读音方式的不同(读成入声与非入声),其听觉效果也是差异很大的。特别是入声字,读时短促而直阻,很难分辨,再加上与声母的配合不同,古人将好多不同韵母的入声字都归为一个韵部,听起来也有它和谐的成分。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音也在变化发展,作诗用的韵表也由《平水韵》逐渐演变到《词林正韵》《中原音韵》及今天的《诗韵新编》与《中华新韵》等,每种韵表,由于语音的变化与方言的不同,都存在着缺陷漏洞和不足,就是新声韵,也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运用时,要根据各个韵表的特点,择其优点,避其缺点,在遵守法则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灵活选择新韵与古韵极其和谐的韵字。也希望新韵的缺憾与不足,能够根据韵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加以完善。顺便说一下,不管怎样完善,但不能出现错误,像《中华通韵》那样出现明显错误的韵表,是完全不可取的,也值不得向社会推广。
依我个人的体会是:作一首诗或词或曲,有一个特别好的句子或词语或韵,必须得用新韵或古韵才合律时,我就根据它们来作取舍,选择应该用新韵或者古韵。确定韵后,灵活选择和谐的韵字,摈弃不和谐的韵字不用,这是我一直以来选韵用韵的原则和方法,提供给大家,可作参考。
平水韵、词林正韵、中原音韵,都是古人曾经作诗所采用的依据,并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将成为千秋万代历史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这些韵,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只能遵守,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修改和抛弃它,它们将与古典诗词作品共同存在于历史长河中,每一个热爱古诗词的人,都应该对它们要有所了解,才能更深刻的体会出古人作品的美感来。所以古韵规则和入声字,将与古诗词作品共同传承于历史长河,万代千秋后也将永不泯灭。有人认为现代汉语的读音,已经没有了入声,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本人看了叶嘉莹先生吟颂并讲解李白《忆秦娥》的视屏,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然她的读音中,入声却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个事实说明了入声在普通话中是没有消亡的,只是在生活中,人们读到它时,发音方式有所改变而已。入声从诗经开始,一脉相承,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它一直伴随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直到现在人们也能处处可闻,怎么就说它消亡了呢?就是当今的新韵表也应该在保留入声字的同时再注明其该派入第几声,这样才更有利于继承与发展。
关于现代人作诗,我们当然可以保留《古韵》并运用其规则,写出具当代人生活信息和思想感情的优秀作品;也可以依据古人诗、词、曲遗留下来的格律及谱,运用现代语音《新韵》的特点和规律,写出适合并具有现代语音特色规律和音韵美感的新作品。两条作诗的道路都是可行的,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习惯和爱好自由选择。但不知古难以正确的认识今,古人留下的东西,我们还是有责任对它进行了解与传承的,像入声这样,一直都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东西,实在不应该丢弃。像《中华通韵》那样完全抛弃入声字的作法,是完全不可取的。保留并继承入声,应是诗词发展中的必然。
在运用《古韵》作诗时,必须得严格遵循其规则,在符合规则的原则下,选择韵字,尽量避免一些与现代读音极不和谐的韵字。有些字的读音,在那个时代组合在一起,读起来是和谐的,但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并还原它们的读音,弄在一起当韵,读起来差别很大,已经很不和谐了,比如 “ü、u”韵,用时尽量不要混用,即使要混用,也可以分组隔开,相当于换韵的方法来用,这样既符合规则,读来也要好听和谐些。《古韵》把我们今天读起来在同韵母上的字,有些分得太细,这也不是他们有意要搞得那样复杂,而是在当时读起来它们的音韵是有所不同而不谐调的,如今我们读起来和谐了,再按他们的要求来用,总认为不合理而又觉得韵太窄,这时,你可以选择使用《诗韵新编》或《新韵》。
关于“ü、u”韵,楚山先生提示我:“ü、u”韵,在古音中两者的主要元音、韵尾是相同或相近的,古代的“ü”韵是圆口音,与“u”韵大多相同、有的相近。今天普通话的“u”韵也是圆口音,但有别于古代的圆口音,而“ü”韵却也变为扁口音,所以差别特大。我试着改变一下口形去体会“ü”韵字的读音,感觉它与“u”韵字音就和谐多了。这个提示很重要,很有价值,为我们还原“ü、u”韵,并充分理解和体会古人作品的韵音美,提供了一把金钥匙,在此深表谢意。
《中华新韵》也有许多不和谐的地方,有待改进,其中最不和谐的是把“eng, ing, ong,iong”混用在一起。南方人几乎不能接受,北方人,通过我的了解,有少部分能接受,但多数人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差异,并认为混用是不和谐的。所以我建议以后重修《中华新韵》时和一直坚持用新韵作诗的朋友们,最好把“ing”和“ong,iong”分成两个韵部,eng则可根据每个字的具体读音,分别派入ing与ong中。关于eng,由于声母的不同,有的与ing较为接近,有的则又与ong接近些,比如声母是f、p、m、w的,就较与ong更接近。如果能将eng分得更客观合理些,也就相对和谐了。
我自己作诗,喜欢采用古韵,原因是入声字的仄用,读起来相当和谐美妙,那种音韵美的感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这是读古人作品久了,不自觉当中得到的一种认同感与美妙体会,入声仄用,由发音规律与方式决定,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仄声是由声音的阻、短、急、促来决定,而不能纯粹地以音调来决定。但自己用古韵作诗时,也感觉古韵把有些同韵部的字分得太细,有时感觉到韵太窄,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不得已而改用新韵,常常为此而遗憾,这也是古韵爱好者们常有的遗憾。不过有条路可以折中,那就是选用《诗韵新编》韵,它保留了入声仄用,读音又采用了现代语音的规律和特点,eng,、ing与ong,、iong也分成了两个韵部,这是古韵爱好者作诗用韵相对合理的选择。不过目前还没能全面普及和得到古韵爱好者的普遍认同,有待推广。但本人感觉《诗韵新编》韵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太死守韵部:像“衣与鱼”本身是和谐的而没归入一个韵部;还有就是笼统地将eng韵部的字全部归入ing,这也是不客观的,也是其遗憾之一。或许这些缺憾,也是其未能得到普遍认同和全面推广的原因之一吧。
关于ing,eng,ong这几个韵,的确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因为受古人用韵的影响,所以争论很大。具体到一首诗,将其相融,至于和谐与否,与其文字组合的先后顺序和所处位置都有很大的关系,好坏只能靠自己的感悟,这就更加复杂了。首先得肯定,它们是邻韵,存在着一些相同的和谐因素,在诗经中还有将后鼻音ang、ing、ong韵的一些字混用的先例,但具体到每个字,由于声母与本身发音的不同,再加上古今读音的变化,其差别也是存在的。至于要怎么分才更合理,肯定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探究。
至于“荣、兄、茕”,古人将其归为8庚,是因为古人的主流语音的读法肯定与现代普通话的读音不同,我们这里的方言就有把“光荣”读成“guāngyíng”的,这几个个例不能说明ong iong与 ing就是和谐可押韵的。
关于白居易的这几句诗:“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有人提到“扃”与“成、惊”押韵问题,首先它不是格律诗,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范畴,即便是作为绝句来说,那怕这样押了,“扃”字处也是弱韵的地方,用仄时可以不押韵,押平韵时,常常可以用邻韵,叫“飞雁出群”。“扃”可以看成是“成、惊”的邻韵借用,或“扃”那时的读音与现在不同,所以这些个例,还是不能说明ong iong与 ing就是和谐可押韵的。
音韵和谐与否,是一个相对概念,在an、en;i、-i、ü;in、ing;en、eng;ao、ou;ing、ang、eng、ong六组韵中,它们之间明显地存在着和谐因素,也有不和谐的因素,具体和谐与否,与古今读音变化、方言有关,还与人对音韵的敏感程度有关,有少部分五音不全,音感差的人就很难感觉不出它们的差异来,而认为它们是可以押韵的,像这类人古今都有,他们也有作品留下来,但数量不多,不要以这类少数的作品来判定它们就是和谐可押韵的。人们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它们同时存在着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因素,具体和谐与否,或要怎样组合才更合情理,在当下,则要考虑它们和谐的百公比,或当今多数人的感觉与趋向来确定,这样才能制定出一个相对完善的《今韵表》来供今人使用,这任重而道远,有待仁人志士们的共同努力。
以上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敷浅认识,拿来与各位同仁进行交流,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2019年12月成稿于花溪河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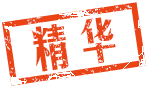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东方旅游文化网
( 苏ICP备10083277号|![]()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
苏公网安备 32080302000142号 )